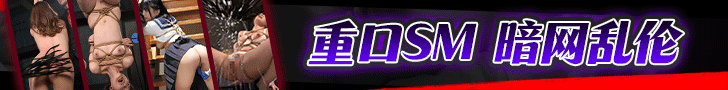司马昭的衣襟散开,靠在兄长怀里,像是在向先祖们宣示他们的乱伦行径。
他头一次感受到背德的羞耻,但司马师已经太了解他的身体,按在小腹上的手往下,握住了他腿间还软着的性器。
被哥哥揉弄几下之后,司马昭很自然的就硬了。
司马师的手指擦过顶端的小口,逗弄着引出粘液。司马昭咬牙忍住呻吟,他小腹绷得很紧,但腰上的力气已经松懈些许,靠着司马师大腿的支撑才没有滑坐下去。
哥哥的手心正贴住他的冠头摩擦,他感觉头脑一阵一阵的发昏,无措间抓住了兄长的手臂:“哥哥……爹,他在看着……啊!”
他仰头靠在兄长的肩上,终于还是叫了出来。而司马师也在同时侧过头,给了他今日的第一个吻。
颊边的温热还没有褪去,司马师的手就绕到了他身后,草草开拓两下,便用性器顶了进去。
向来他们交欢,兄长都会准备得很周全,这次的插入却像鞭挞一般,没有脂膏也没有多少扩张,让司马昭久违地感受到了疼痛。
其实疼也不算什么,真的不算什么,兄长的用意他已经明白了。
抽插几下后,司马师拔了出来,抱着他,给他转了个身。他和兄长四目相对,而那些审视他的灵位都在他身后,他看不见了。
再次插入的时候,司马师慢了下来。司马昭抱住他的脖子,脑袋埋在他颈窝;而司马师拥住了弟弟,他的手掌按在司马昭的后脑。
他们相依相存一样地拥抱着,司马昭随着兄长的顶弄而颠簸,在颠簸中愈发紧紧地抱住了兄长。
在被情欲吞没之前,他听见哥哥的声音:
“昭儿,错了就要付出代价。”
“但是,哥哥不会让你的付出白费。”
东兴的耻辱次年在新城被洗刷,同时司马昭也因抵御蜀军、平叛有功,爵位恢复如初。然而之后司马师的废立之举,又激起了镇东将军毋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的反叛。毋丘俭在檄文里面把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昭司马望一顿夸赞,独独贬低了司马师。
谁都看得出来这是在挑拨离间,但明显的挑拨不见得就无效。
司马昭说,我去吧,兄长你留在洛阳。
然而刚刚做了除瘤术、眼前还蒙着白布的司马师摇头:“我去,不能出差错。”
正如傅嘏所言:“淮、楚兵劲,而俭等负力远斗,其锋未易当也。若诸将战有利钝,大势一失,则公事败矣。”此战确实容不得闪失,司马师舆疾而东,临行前令司马昭兼任中领军,留镇洛阳。
没过多久叛乱平了,但司马师没有回来,司马昭被一封家书召到了许昌。
大将军的印玺被交到他手中,兄长覆在他手背的掌心冰冷。司马师的左目被白布遮掩,白布被血迹浸透,还可以看向弟弟的右眼却是平静的。
他说,昭儿来得真快。
他说,这方印是你的了。
他说,把我摆到父亲旁边,我会看着昭儿……
司马昭人生的容错率终于达到了最低点。
小皇帝想借机夺权,令司马昭镇守许昌。但司马昭无比冷静,就像哥哥生前那样冷静,他听从了傅嘏和钟会的建议,自己率领军队回了洛阳。
后来淮南再再叛乱,司马昭的运气比父兄好上许多,他带着皇帝太后直奔扬州,平叛后不仅性命无忧,而且惊喜地发现,已经没有多少魏室忠臣了。
他会在哥哥的路上,走得比哥哥更远。
但世事又怎能尽如人意?不仅司马昭,皇帝也惊恐地发现朝臣已经多是司马氏的人。十九岁的少年天子,正在热血沸腾的年纪,架着战车直闯大将军府,想做夏少康。但是天下已经没有有虞氏了,于是小皇帝最后成了刀下鬼。
司马昭当然是不愿意的,弑君这是多大的罪名啊!
他仿佛回到了东兴战后,他对着旧友陈泰恸哭:“玄伯,其如我何?”
陈泰回:“独有斩贾充,少可以谢天下耳。”
但是他怎么能杀贾充呢?当年兄长甚至都没有免去胡遵王昶他们的官职。
他沉默良久,止住了哭泣,盯住陈泰道:“卿更思其次。”
陈泰和当年的王仪一样不给他面子:“泰言惟有进於此,不知其次。”
但是大将军必须要一个其次。司马昭推出成济做替罪羊,自以为处理得还算得当,但到底还是因此失去了一个故人。
或许不止一个故人。
司马昭想过,如果兄长还在,一定不会让事态发展至此。但弑君的骂名已经背了,错了就是错了,他会背负代价,继续走下去。
后来司马昭还是做对了很多事,比如伐蜀,这也让他在父兄的基业之上走得更远。
兄长过世十年后,他接受了晋王封号和九锡,他想起遥远的建安年间,想起另一个加九锡的权臣,或许他应该称呼那位权臣“先武帝”。
但是很快,他或许也要成为“先x帝”了。
司马昭跪在祠堂里,他和哥哥的灵位相对。
他说,子元,你都看见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