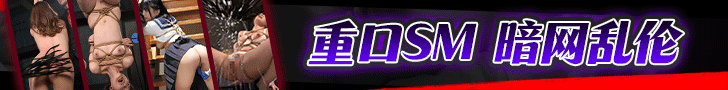徐若凝头疼得睡不着,爬起来要抽烟。
谢屹诚把她揽进怀里,见她眼眶通红,低头亲了亲她的脸,把她抱在怀里,温热的掌抚着她的头发,声音低低地说:“我以前接触一个案例,一对情侣到外地旅游,男朋友被杀害,女方成第一嫌疑人。”
换作平时,徐若凝肯定要笑死,谁会在事后跟女伴讲这么血腥的案例。
但她涨疼的大脑得到片刻缓冲,情绪慢慢平静下来,安静地趴在男人怀里听他低醇的声音,慢慢细数案子的整个经过。
“女方是我的当事人,我去警局的时候,她还在哭,比起害怕,她似乎更不敢相信自己的男朋友就那么死了……”
“她告诉我,他们分开了一个下午,因为男朋友说要去找一个朋友,而她去商场独自购物了一下午,晚上回酒店的时候,男朋友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,她觉得奇怪,问了他几句,以为他很累,便去洗手间洗漱,回到床上的时候,才发现男朋友已经死了。”
谢屹诚低头看了眼,徐若凝趴在他怀里睡着了。
她惯常笑得张扬又热烈,一张嘴天不怕地不怕,眉眼间的笑浓得像酒,让人只一眼便深陷其中,醉意醺醺然。
但谁能想到,她闭上眼睡着的样子会这样乖巧。
他伸手摸了摸她的脸,把灯关掉,将人搂得紧了些,闭上眼缓缓睡去。
第二天还不到十点,徐若凝的手机响起来,她被吵得头疼,摸到手机就砸了出去。
谢屹诚下了床把手机捡起来,看了眼,备注写着徐风塘。
他走到床边,摸了摸她的脸,声音很低,“你家里人的电话。”
徐若凝从被窝里爬出来,眯着眼看了他一会,伸手接过电话,滑动放在耳边,电话是徐父打来的,问她什么时候回去,要不要回家里吃个饭再走。
徐若凝声音很哑,“不去了。”
徐父那边顿了好一会才说:“是不是感冒了,注意身体,现在天冷……你一个人好好照顾好自己。”
徐若凝只“嗯”了声,便再没有话要讲。
气氛沉默下来,徐若凝问:“还有事吗?”
徐父干笑了一声,“你忙吧,我就问问,你要是没时间就,就算了。”
电话挂断,徐若凝扔了手机继续睡。
没一会爬起来,问谢屹诚要烟,谢屹诚没理她,把人捞出来抱到洗手间洗澡。
她想说话,男人就把牙刷挤上牙膏塞进她嘴里。
她懒懒地站在那,嘴里含着牙刷,仰着脸就能看见身后的男人,他一手环着她的腰,扶着她站稳,另一只手拿着牙刷刷牙。
两人都没穿衣服,光溜溜的身体贴靠在一起,没一会,他就硬了,灼热的硬物抵着她的后腰。
徐若凝隔着镜子看了他一眼,含着牙刷,声音有些含糊,“还没吃饱呢?”
谢屹诚刷完牙漱口,拿了毛巾擦干净脸,这才用下腹撞了撞她的臀部,声音低低地问:“还有力气吗?”
徐若凝飞快洗漱完,搂着他的脖子,一边仰着脸吻他,一边用双腿缠上他的腰。
男人汹涌地反客为主,薄唇含住她的唇舌,含弄吮咬,硬硬的胡茬磨得她嘴唇又痒又麻,她轻哼着摸他的耳朵,开口的声音带着轻喘:“以后不要刮胡子了。”
谢屹诚深深睨了她一眼,薄唇用力吮咬着她的唇瓣,他一只手扶着她的脊背,热烫的吻沿着她的脖颈往下,停在了那团绵软附近,没伸舌头去舔那硬挺的乳尖,反而是抿着唇用胡茬蹭了一下。
徐若凝脚背绷直,喉腔里发出颤颤的呻吟,“啊……重一点……”
谢屹诚呼吸一重,薄唇抿住那颤栗的乳尖,胡茬重重碾过她的乳肉。
徐若凝整个人哆嗦起来,快感让她不由自主地往后仰,谢屹诚把人抱出来,从她的乳肉一路往下,舔到她的阴户,那儿早就湿漉漉一片。
他用胡茬磨了磨那颗红豆,见它变得颤栗硬挺,薄唇一抿,含在嘴里,复又松开,用胡茬去磨。
徐若凝受不住地抓住他的头发,左右乱扯,脖颈高高仰着,喉口呜咽,生理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等她颤抖着高潮时,男人这才擦了擦莹亮的唇角,握着肿胀到发疼的性器沉身顶入。
快下午,两人才从酒店出来。
徐若凝整个人被掏空,在楼下大厅吃了顿豪迈到令人侧目的午餐后,这才坐在沙发上,闭着眼靠在男人肩上眯了会。
谢屹诚以为她又睡着了,冷不丁徐若凝突然开口问:“你昨晚说的那个男的,到底谁杀的?”
他把大衣拿过来盖在她身上,低头看了她一眼,她眼睛仍闭着。
“情人。”他声音质感低醇,十分好听,“男人在外面有情人,被发现后,情人怒火中烧,随后便设法杀了男人,又嫁祸给了他女友。”
“以后多讲点给我听。”她往他脖颈蹭,声音含糊,“我喜欢听。”
谢屹诚胸腔里溢出笑声。
“笑
什么。”她伸手扯他的脸,动作透着股孩子气。
谢屹诚曾经被家里安排过相亲,在他两年前刚回国那段时间,相亲的女孩比他小两岁,性格很温婉恬静,因为他一直不爱讲话,她便开口让他挑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说。
于是,谢屹诚就讲了个回国刚接触的一个案例。
再然后,女孩去洗手间吐了两遍,面色苍白地离开了。
昨晚他只是想让徐若凝分神,没想到她会听案例听睡着,更没想到,她居然喜欢听这些血腥案例。
因而,他忍不住想笑。
“我晚上要回家一趟。”他低头看她,问:“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?”
徐若凝睁开眼,她看了他一会,说:“你相信算命的吗?”
谢屹诚:“……”
“算命的说我晚婚晚育,你妈要是不催的话,我们晚点见也行。”徐若凝摸了摸自己的肚子,“我暂时还没有怀孕的打算。”
谢屹诚看了她肚子一眼,唇角轻扯,“你害怕见她?”
“开什么玩笑。”徐若凝拨了拨自己的头发,“我怕我魅力太大,老太太一眼看见我就抓着我不放,我跟你讲,我很招老头老太太喜欢的。”
“嗯。”谢屹诚摸了摸她的脸,忍不住低头啄吻了下她的唇。
声音很低:“是很招人喜欢。”
徐若凝:“……”
她蹭过去,咬他的下嘴唇。
“谢屹诚。”她声音从齿关溢出来,带着笑,“你让我脸红了。”
他大掌扣在她脑后,把吻加深。
他没刮胡子,胡茬硬硬地磨着她的唇瓣,一吻结束,徐若凝嘴唇都被磨得火辣辣,她掏出唇膏擦了擦。
谢屹诚偏头看她,徐若凝挑着眉问他,“看过周星驰和张柏芝那个电影没有?”
不等男人回答,她又凑过来,用自己涂完唇膏的嘴唇往男人薄唇上蹭了蹭,“好了。”
她把润唇膏放包里,拉着谢屹诚要起来。
男人却伸手将她拉坐在腿上,徐若凝一屁股直接坐在炙热的硬物上,她扭头看了男人一眼,忍不住问他:“你老实告诉我,你到底多久没做了?”
谢屹诚低头埋在她肩颈的位置,唇角微扯,很轻地笑了声。
下过雨的天儿潮气很重,微风都透着股凉意,徐若凝走出酒店门口,被冷风激得缩了缩脖子。
谢屹诚把手里的围巾缠在她脖子上,刚刚在酒店,他让她戴上,她死活不戴,说太热了。
这下倒好,冻得直往他怀里钻,嘴里还喊:“哎呀,今儿风好大啊,怎么把我吹别人怀里了呢。”
谢屹诚:“……”
等男人给她戴好围巾,徐若凝这才笑着到路口打了车,看着谢屹诚坐进去,这才冲他挥手。
车子刚消失在眼前,她就从包里摸出烟。
只是刚点上,还没来得及吸,就接到谢屹诚电话,男人声音和缓,带着股令人安心的力量。
“别抽烟,我很快回来。”
徐若凝指尖顿了顿,她看着出租车离开的方向,唇角扬起笑。
她把烟掐了,仰起的那张脸上,一双瞳仁泛着柔和的光。
“那你要快点。”
“不然我会想你。”
徐若凝还是回了趟家。
徐父一开门看见她,怔愣过后,一张脸很快爬满笑意,“宁宁来了啊?快,进来。”
徐若凝手里提了些东西,超市还有不少年货,她随意买了几样,进来也没换鞋子,径直往客厅的方向走。
家里这几天应该来了不少亲戚,客厅上摆满了瓜子花生和糖果,地上还有瓜子壳没打扫。
洗手间传来抽水马桶的声音,徐若凝以为是后妈,没想到门开之后,看见了徐以知,他还在读大学,六月份就毕业了。
看见徐若凝,他愣了很久,才认出她,礼貌地喊了声,“姐,你回来了。”
徐若凝没什么表情,她跟他并没有多熟络,也没什么感情,后妈防她跟防什么一样,生怕她不知不觉就把徐以知给弄死。
十八岁那年,徐若凝离开家就没回来过,如今过去十年,难为他还认得她。
他个头清瘦,长相和徐风塘并不像,反倒是比较像那位后妈,小时候还有些顽皮,身上带着被宠坏的傲气,倒是长大了,收敛了不少。
徐若凝“嗯”了声,走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眼,屋子里大概这两天被打扫过,到处都很干净,衣柜里她的衣服也都还在,洗到发旧的校服和球鞋。
仿佛看见了曾经窝在这个房间里,每天只知道埋头苦读的女生。
她视线一点点掠过房间的角角落落,身后徐父过来问:“回来就住几天吧,你房间都打扫过了,你妈她出去了,一会回来。”
没回来挺好的,徐若凝不想看见她。
她从包里拿出一沓现金放在桌上,她工作以后,每年都会转账给父母,一开始双方都没收,后来徐若凝就
往他们卡里打钱。
母亲几年前也曾打电话,话里话外想见她一面,徐若凝边抽烟边回了句:“没空,忙。”
她确实忙,也有意让自己忙。
孤鸟不能停下来,停下来就会让人发现它是孤独的。
徐父把钱往她包里塞,“不要,你给很多钱了,你一个人在外面那么辛苦,以后就不要给我打钱了。”
徐若凝没管他,等他把钱塞进包里,又把钱拿出来放在茶几上。
徐以知看着这一幕没说话,他坐在沙发上,剥着瓜子,细长的手剥下瓜子仁,一粒一粒放在纸巾上。
徐若凝曾经欺负过这个弟弟,使唤他给自己剥瓜子,就那么一次,她请他吃完雪糕,他坐在边上,小小的手笨拙地给她剥瓜子。
那天父母不在家,让她去学校接弟弟,他们坐在楼下等。
后妈不允许徐以知吃雪糕,因为他小时候身体不好,总是生病,时常闹肚子,生冷的东西一概不允许他吃。
徐若凝记得,那时候才六岁大的徐以知舔着雪糕,笑着冲她说:“姐,你真好。”
徐若凝却撇开视线看向别处。
她不喜欢他,这个从出生就抢走她父亲的人。
如今长大了,看见这一家子人,她的内心也没什么触动,只是有些压抑,她不喜欢看父亲脸上那种愧疚不安的表情,更不喜欢徐以知一副做错事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说到底,她就是个外人。
她把钱放下,临走前,把纸巾上的瓜子抓了一把,徐以知诧异地看向她,眼底隐隐有笑。
“走了。”她往外走。
徐父跟出来,“你没事去看看你妈,她……身体不太好,前阵子生了病。”
“她不是有子女么?”徐若凝声音不咸不淡。
徐父轻轻叹了声,“久病床前无孝子,她这场病,病太久了。”
徐若凝回头看他,忽然喊了声,“爸。”
徐父激动地应了声,“哎。”
“你后悔吗?”她问。
徐父明白她问的是自己年轻时,为了钱跟徐母吵架离婚的事儿。
他自然是后悔的。
但是为人父母,自然不敢将心里真实想法告诉孩子,他轻叹一声说:“有什么后不后悔的。”
徐若凝看着他花白的头发,轻轻笑了,她头也不回地下楼,只声音淡淡传来:“你回去吧。”
徐父追了两步,“你不留在家过两天吗?下次什么时候来?你去看你妈吗?宁宁?宁宁?”
徐若凝已经不再回应。
徐父追到楼下,徐若凝已经走远了,她潇洒地坐进出租车里,司机开了车直接就走了。
徐父在原地站了很久才回到家里,沙发上,徐以知还在剥瓜子,看见他一个人回来,他默默地把纸巾上的瓜子捏在手心。
这个家太安静了。
徐父时常落寞后悔,哪怕他当初自私一点,多为徐若凝做一些,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局面。
他又想起孩子问的那句:“你后悔吗?”
他走进房间,深深叹了口气。
徐若凝嘴上说不去看,到底坐车去了医院。
母亲嫁了个有钱人,只是日子并不好过,因为是二婚,又在外面生过孩子,在家里受尽婆婆的刁难。
财政大权也不归她,只等她生下一双儿女,这才有了张卡,里面是每个月的生活费。
徐若凝十四岁那年,特别想她,曾偷偷跑来看过她,母亲带她去了麦当劳吃东西,又匆匆把她送走,担心被婆婆发现,更担心自己的孩子发现。
巧的是,母亲当时和后妈想法一样,搬家到陌生的城市,结果误打误撞,一个搬到新城,一个搬到新城的市中心,离一小时车程。
徐若凝坐在车上昏昏欲睡,脑子里想起很多小时候的片段,零散的,像无声的黑白电影,一幕幕从眼前掠过。
她心如止水地看着窗外,眼皮微微垂着,想从包里拿烟,脑海里无端想起男人那句话,又默默从包里摸出一根棒棒糖,撕开塞进嘴里。
她进医院已经是傍晚,天已经黑了,她去护士站报了姓名,找到母亲的住院病房,就站在门口看了会。
母亲一个人住单人病房,旁边就一个护工,子女不在,桌上有花篮和水果,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,神色恹恹地看着电视。
徐若凝出门买了包瓜子,找了椅子就坐在门口,边磕,边陪着里面的人一起看了场无声的电视剧。
谢屹诚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,问她在哪儿。
徐若凝看了眼周围,说:“医院。”
“怎么去医院了?”他问,“哪里不舒服?”
“肚子。”徐若凝把身上的瓜子壳拍了拍,低下来把地上的壳儿捡干净,一并丢进垃圾桶,这才冲电话那头道:“医生说里面长了个东西。”
“什么东西?”
徐若凝压低声音说:“就是精子和卵子
结合后长出来的那玩意。”
谢屹诚:“……”
“怎么不问了?”她笑起来。
那头男人声音很正经,“定位发我。”